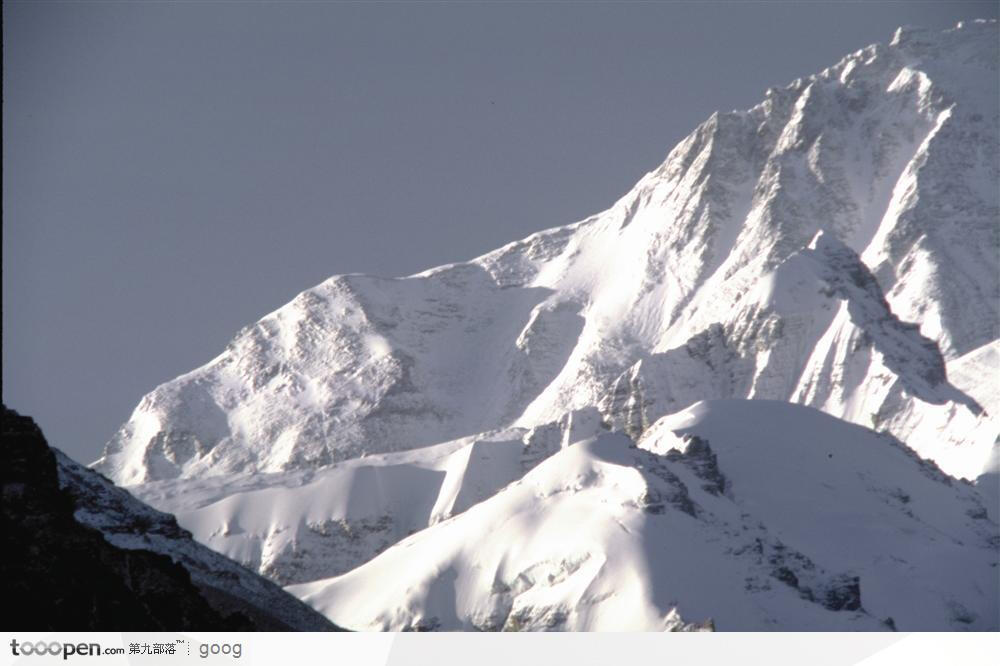好了,不用一一再看其它的书了。其实,我早就看过一些关于紅軍的書,只是沒有特別注意過黑水蘆花。現在,身處黑水蘆花的我談到那些關於黑水蘆花的文字,感覺到了自己體內的汩汩熱流。
想必蘇朗彭初的體內也有汩汩熱流湧動,他在看過的那些書裡都作了記號,書頁中有他藍筆紅筆畫的符號或者在書頁上打了折疊。他很想弄清當年紅軍在他家經歷的所有細節。比如,他祖父澤旺頭人生前回憶:“1935年7月23日,一早,紅軍在我家前面大草坪上,召開了萬人大會,處決了兩名紅軍,就離開了。我帶路往沙石多、昌德,那晚在昌德住。”那兩名紅軍為何被處決?聽說是違反了群眾紀律,受到了最嚴厲的懲罰。但兩名紅軍違反群眾紀律的具體情節是怎樣的?蘇朗彭初為那兩名紅軍感到惋惜,他一直想去檔案館查一查,但不知哪里的檔案館才會有這個資料。他嘆息,很心痛,很糾結,甚至想過如果能查到資料,一定要帶點黑水蘆花的土特產去安慰一下那兩名紅軍的後人:“哎,不管怎樣,他們兩個畢竟是背井離鄉參加紅軍的,不容易啊。”
還有一件令蘇朗彭初糾結的事,他聽父親講過,當年紅軍在他家前面的大草坪上分完糧食和物資後,“紅軍首長”送給澤旺頭人兩張布幣權作“借條”,說:“你好好保存,將來會加倍地還你。”蘇朗彭初並沒有想過要紅軍還什麼,但他一直記著這件事,從少年開始就想見到那兩張布幣。也許是神靈保佑,或者是菩薩也為之感動,動了惻隱之心,賜給蘇朗彭初一個不費勁就見到“借條”的機會。蘇朗彭初說:“我女兒的床是靠著牆壁的,那幾天老是有老鼠把她的衣服、毛巾拖進牆角洞裡。我一氣之下就想要掏掉老鼠的窩。我把幾塊磚拉出來,把手伸進去掏,卻在洞裡發現了一個瓶子。瓶子是黑色的,能裝半斤水,裡面就放了這兩張借條。”他還興奮地告訴我,剛開始他並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,拿去問別人,別人說可能是佛教方面的東西,但細看,上面印的又是漢字,這下誰也說不準了。後經有關部門鑑定,確認是紅軍使用過的布幣。他向我展示了“借條”:深藍色的布條,長約3寸,寬2寸許,上有繁體字“中國工農紅軍”、“川陝省蘇維埃政府•三串”,並蓋有印章。有人認為這是可以賣出好價錢的東西,建議他賣掉,以補貼家用。他一聽,眼睛瞪得贼大:“那咋行,不能賣,要是光想錢,紅軍開蘆花會議的這幢房子我早就賣了。這都是屬於紅色文化的東西,一賣成錢,紅色文化就變顏色了。”他留下一張布幣作為“蘆花會址”展覽用,另一張捐獻給了國家的革命軍事博物館,得到一本“捐獻證書”,這讓他很釋懷。
但是蘇朗彭初仍有一個很大的遺憾,當年紅軍離開這裡時還送給澤旺頭人一支步槍,澤旺頭人把槍放在地下室,卻被佣人發現了,並且偷偷地拿去賣了,沒有保存下來。“只怪我祖父的心太好了,要是換了兇的主人,還有哪個佣人敢偷主人的東西?”他至今說起這件事還忿忿然。
好在還是多少保存下來一些紅軍的遺物,這些遺物對於蘇朗彭初來說,真的就是“映山紅”,只要他每天每天守護著這些遺物,就是盼到了紅軍來。那麼,他的妻子索朗俄滿唱的“映山紅”就別有一番意味,別有一番道理。那就讓我們一起唱:“若要盼得哟紅軍來,嶺上開遍哟映山紅……”
今天,蘇朗彭初精心守護的“蘆花會址”還在演繹著這支歌。我熱切地盼望傅庚辰政委來這裡聽一聽他創作的這支歌,喜歡這支歌的人都來聽一聽吧……
索朗俄滿在二樓的廚房忙著做飯招待我和陪同我去採訪的劉飛,這時蘆花鎮的紀委書記格馬趕來了。格馬書記很佩服蘇朗彭初守護“蘆花會址”的堅定意志,他說:“如果不是為了守護這裡,蘇朗彭初的生活不會象現在這麼艱難,他三個孩子的生活、學費是一個很重的負擔,前幾年他外出打工掙的錢,還有大地震後政府補助的錢,都用於維修蘆花會址了。有的人對此不理解,我能夠理解;有的人說不值得,我認為值得。但是他守護得太難,太難太難了,似乎不亞於當年紅軍遇到的經濟困難,而紅軍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那種精神,正是他想學習和傳承的。”
確實太難。現在來這裡參觀的人越來越多,蘇朗彭初為佈置展覽室也花了不少錢,費了不少心思。為了使展覽室的空間大一點,還有使“蘆花會址”的會議室空間大一點,他在碉樓前面的圍牆邊上搭了三個棚子,把家裡的許多東西都堆放在棚子裡。我和劉飛在白天去察看了棚子,裡面的東西基本發霉。我摸了摸一個沒有開箱的太陽能熱水器:“為什麼不安裝在家裡呢?”蘇朗彭初說:“這是政府給每家發的,個人出500元,我怕安裝以後會破壞蘆花會址的原貌。這裡可是國務院評定的重點革命歷史文物,我寧願太陽能熱水器廢掉,也不能讓革命歷史文物受損。”我看著從發霉的家具縫隙裡擠伸出來的長長植物,感覺它們正在靜靜地向我傾訴著什麼……
我向蘇朗彭初建議:“你可以在展覽室放個捐款箱,說不定有人會伸出援助之手。”他搖頭,說過去也有人這麼建議,他就做了一個小捐款箱,但隨後一想,不能讓別人說三道四,以為他利用“蘆花會址”攫取財富,就把捐款箱燒了。也有一些人承諾要幫助他,但承諾之後便再無動静,他從剛開始的激動變為麻木,甚至反感了。他說,有時候到了夜晚,他就獨自坐在陽台上苦思苦想:“80年前在這個陽台上坐著的‘紅軍首長’,是不是也像我現在這樣想問題的?”想着想着,他會默默地流淚……
索朗俄滿已經把飯菜做好,年僅9歲的小兒子澤朗旦木真沿著陡斜的木梯,不斷地端著飯菜跑上跑下,這讓我想起澤旺頭人生前的回憶:“當年紅軍在三樓開了大半天會,一些小紅軍跑上跑下,忙了一天……”我眼睛一亮:當年那些小紅軍的身影就疊印在澤朗旦木真的身上。
我們邊吃邊聊。按藏族人的習慣,客人到家裡吃飯是一定要喝酒的,但為了保持“紅色守護人”的“正規”形象,蘇朗彭初已經堅決戒酒好幾年了,真正做到了滴酒不沾。他以飲料代酒敬我們。席間,他說這幾年他自費去北京有十多趟,但從不去旅遊景點,而是去拜訪博古、徐海東、王定國、萬海峰、張敏、朱位漢、蒲文清、房楊達、向守志、黃靜波等老紅軍,然後去文物市場淘點“紅色文物”。有段時間妻子索朗俄滿對他不理解,埋怨他是不是瘋了,是不是老紅軍附身了?他不多解釋,只承認自己是瘋了,是老紅軍附身了,而且附身的不是一個,而是一群。有一次他從北京背著沉重的背包回到家,妻子和女兒歡喜地迎上去,以為他給家人帶回了什麼禮物,激動無比地解開背包一看,妻子和女兒們一下傻了,兩個女兒失望地走開,妻子小聲說了一句:“又收了一堆廢品。”說完,妻子眼裡的淚水就刷刷地流。他看著日漸消瘦的妻子委屈的樣子,也忍不住淚流滿面。兩個淚人就那麼不出聲地站在那兒,就那麼歉意地看著對方,然後輕輕地牽著手,走進他們家族四代守護的這個房門……從那以後,家人們對他的背包再無半點興趣了,但他說,總有一天,家人們對他所做的一切都會感興趣。